反特片叙事裂隙对比研究——从《英雄虎胆》到《雾都茫茫》
提要
作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反特类型影片随着社会变革和发展呈现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叙事裂隙。以《英雄虎胆》和《雾都茫茫》为代表,反特片的叙事和表达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经历了微妙的转变,主要通过外在元素、“美人计”、凝视、符号隐喻、“死亡”结局等要素完成硬性政治要求下叙事裂隙由弱到强的呈现,一方面印证了改革开放后社会意识形态由政治一元化向消费娱乐化、自由化的转变,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裂隙中积极的女性个体与倒退的性缘模式的矛盾化交织。
一、裂隙的意识形态转变:从政治的一元化到消费的娱乐化、自由化
反特片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电影种类,活跃于20世纪50年代,以“十七年”历史时期最为出名,而经历文革至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反特片虽然社会影响力远不如前,也不乏讨论的价值。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反特片反映了不同社会阶段变化的意识形态,其叙事裂隙正是建立在固有的宏大意识形态框架下,由电影创作者的输出到接收者的二次解读和消费之间形成的复杂偏差。50年代的意识形态以政治上的一元化为固定准则,中美、国共矛盾呈绝对的二元对立模式,80年代的意识形态建立在改革开放的新思潮之上,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传统反特片中尖锐的政治斗争被弱化,矛盾重心转向保卫国家安全的工作,同时受消费主义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娱乐化、自由化,具体到影片中主要体现在外在元素、“美人计”和凝视三方面。
1、外在元素的开放性
外在元素是反特片中敌我界限的重要分辨途径,表现在服饰、发型、神态、生活作风等方面,帮助观众区别敌我、判断善恶和正邪的直接表征。20世纪50年代的反特片极度重视分明的敌我界限和二元对立的外在表达,80年代则在消费主义浪潮下加入了相应的商业片元素,更加强调观赏性,对我方侦察英雄的塑造也更具自由度和开放性,他们在敌区可以穿西装、吃喝玩乐,融入上流社会的生活。作为80年代反特片的代表,《雾都茫茫》前段用了长达四分钟的时间来表现跳探戈、学英语的场景。这些在50年代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只有反派、特务们才能“享受”的生活,如《英雄虎胆》中的李月桂,穿真丝睡衣、弹琴、喝洋酒,服饰言行处处透露出资产阶级做派,具备一眼就能看穿的典型腐朽形象的特点(图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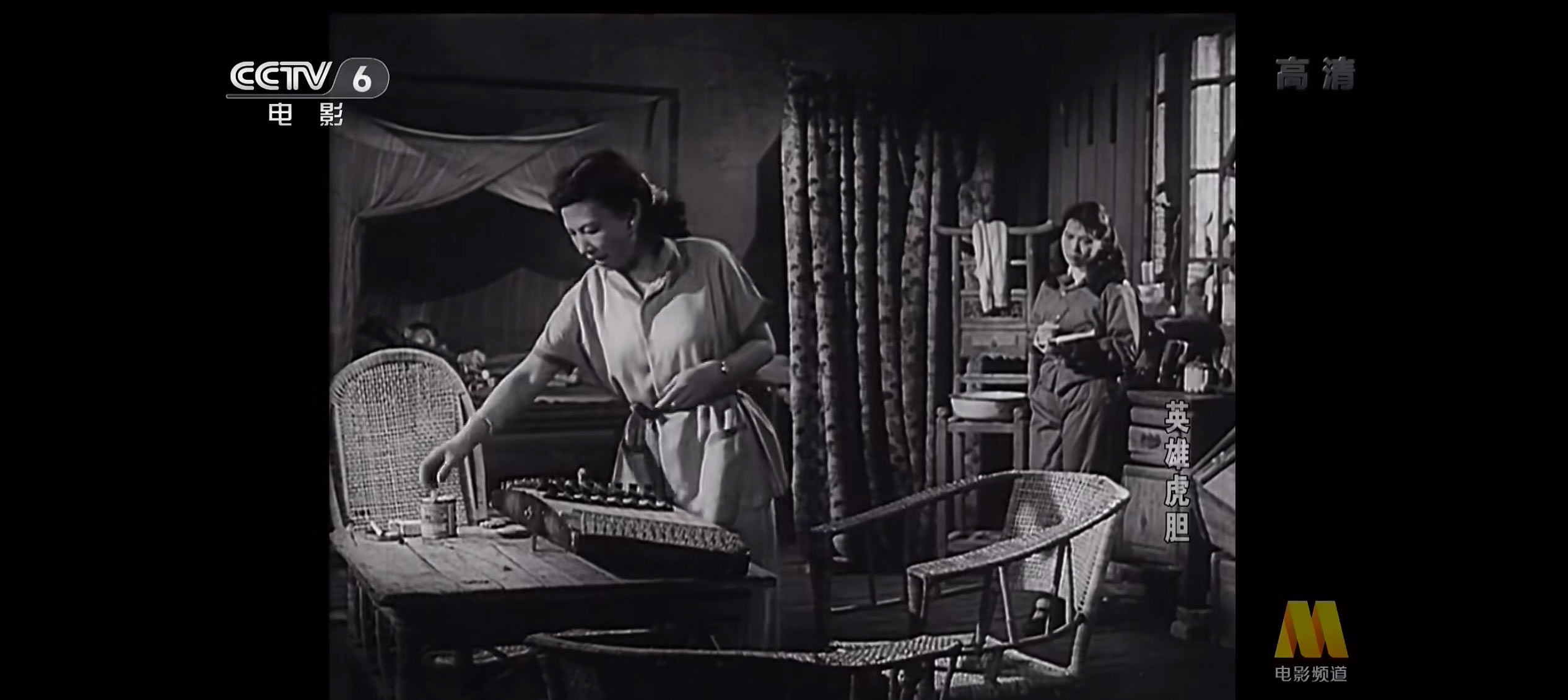
《英雄虎胆》和《雾都茫茫》都有跳舞的场景,在这两场相似的场景中,导演对围观群众动作、神态的刻画也不尽相同。《英雄虎胆》中曾泰和阿兰跳伦巴时,周围的土匪们的面容都被刻意夸张和丑化(图2-3),尽显糜烂的生活作风,令人生厌,而《雾都茫茫》中沈兰和林晶跳舞时,周围观众的表现都礼貌克制,且能很平常地表现出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图4),没有过分强调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甚至给观者营造出少许浪漫、美好的氛围。外在元素的差异源自80年代社会风气的开放,也侧面印证了对反特片道德判断的标准不再单一而死板。


2、“美人计”的主动性
反特片常用“美人计”模式。50年代传统反特片的“美人计”往往都是敌方特务主动出击或勾引,我方被迫深入虎穴,机智应对,且都是敌方“女”特务引诱我方“男”英雄,没有出现过敌方“男”特务引诱我方“女”英雄或我方特务主动使用“美人计”。在当时以政治认同为首要准则的意识形态下,我方主动对敌方使用“美人计”是一种“不洁”的符号标志,而我方“女”角色主动使用“美人计”接近男特务更是女性“不洁”的标志,不但在身体政治上损害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而且还会冒犯观众的审美定势。《英雄虎胆》中曾泰打入匪首李汉光和李月桂阵营后,阿兰最初是作为李月桂对曾泰打入巢穴进行试探的一枚棋子,这里的“美人计”是由地方女特务阿兰主动出击(图5)。阿兰是政治的符号与性臆想的结合,是公共话语中被批判的“危险女人”的代表,兼容了现代都市舞女、交际花的气质,却不符合当时女特务“妖邪”的刻板塑造标准,因而在获得观众逆反性好评的同时,遭到意识形态的打压。但事实上,她的剧情依旧通过性的呈现、性意识的隐性满足以及观众自我认同的构建完成了“美人计”的叙事递进。

而发展至80年代的反特片,意识形态的政治意味变得更加淡薄,传统“美人计”的僵化模式逐渐打破,我方侦察英雄甚至可以主动出击,他们的破禁被赋予了合法性。我方侦察英雄在《雾都茫茫》中,我方男英雄沈兰为了潜入林家以获取炸毁栾城C-3计划的情报,利用一场车祸救下国民党特务林南轩的女儿林晶(图6),借救命恩人的身份获得了林晶和林南轩的信任。此时我方英雄主动设“计”并“牺牲色相”的行为也不再因为道德上的不完美被钉上意识形态的耻辱柱,虽然整体意识形态仍然保留政治立场的诉求,但反特片已经发展出一种新的生态,即一种消费娱乐的尝试,具备更加自由化的表达。
3、双向凝视
传统反特片的凝视模式是女特务主动勾引、凝视男英雄,而男英雄基本不看女特务,这点在50年代反特片中最为鲜明。女特务的形象呈现着女性自身的性别气质的同时,被用来批判一种腐朽、堕落甚至邪恶的思想,由此呈现作为阶级敌人标志的女性特征及其符号系统,一方面符合50年代政治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同时也符号民间阴阳相生的传统哲学观,彰显男英雄代表的阳刚、崇高的形象。英雄人物可以面对严刑拷打,但如何对付女特务的诱惑这类人们颇感兴趣的问题,在当时“只能‘策略性’地回避,因为英雄人物既不可能严词拒绝,又不可能顺势推舟,前者不真实,后者则有辱英雄的形象”。[1]如《英雄虎胆》中曾泰和阿兰跳伦巴时,阿兰主动凝视曾泰,曾泰却刻意回避她的凝视,脸朝向观众,以此达到政治和私德上的完美(图7)。
《雾都茫茫》中也设置了一场跳舞的剧情。相比曾泰对阿兰凝视的回避,沈兰和林晶跳舞时,没有选择回避林晶的凝视,镜头反复在转圈的两个人之间切换,两个人的目光是望向对方的,虽然林晶眼里的光更鲜活,但此时此刻他们确实是在互相凝视彼此(图8-9),完成了视线的双向交流,以对称的画面满足了观者的观看和想象,达成看与被看的主客体位置的平衡。

在此之前,沈兰和林晶产生第一次视线交流是在影片前段,林晶站在夜晚的路口,沈兰从她面前走过,“不经意”却主动地回头看了她一眼,两人发生了一次象征初遇的对视(图10)——随后一辆车冲向林晶,沈兰为救林晶而受伤。在此之后,沈兰和林晶去电影院、在游船上约会时,两人也有多处视线交汇,相处都十分融洽,不显得刻意,沈兰对林晶的回应不像曾泰对阿兰的回避、随意、冷淡,甚至他经常回应林晶的目光,展露出真挚的笑容(图11-12),给观众一种他们之间确实有真情的美好错觉,满足并增加了观看的娱乐性。


这种视线交流在50年代的反特片中纵有表现意图,显然是缺少表现空间和自由的。同为正派英雄,如果说曾泰潜伏扮演敌方副司令的表情总是带着难以掩饰的对敌方的憎恶和过分的刚直,沈兰的表情则无可挑剔,正邪难辨,极具迷惑性,一定程度消减了英雄形象的扁平化,也为观众的娱乐和个人遐想留有余地,具备文化消费的功能。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将其看作80年代意识形态表达手法的转型——以情感表达区分立场,真情必含蓄,虚情可开放。面对互有好感的战友朱玉菀,沈兰在与她分别时也只有一个握手一句“再见”,视线交流间配以背景音乐里悠扬的“此情此意最长久”(图13);朱玉菀死后沈兰除了在车里呼唤她的名字并流泪没有其余出格的言行,男女感情表达之含蓄,可见一斑。而对林晶这个棋局中的一枚棋子,沈兰则可以回应她的凝视,毫不脸红地说出“我不是不懂爱情,你的心我也非常明白”这样直白而奔放的话,这同时是以其正确的政治立场作为底气的,用以替换早期反特片的道德评判。但无论从何角度,这些对比都可看作从50年代到80年代反特片叙事裂隙扩大的表现,是在保留政治诉求为主导的前提下对个体的多元完善,对娱乐化、自由化表达的尝试。
二、裂隙中的女性个体与性缘模式:积极与倒退并存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女性角色在反特片中的形象设定同样经历了微妙的转变。女性,尤其是女特务形象的叙事裂隙由暗到明,从被动隐蔽逐渐走向被容许的丰富、立体,个体与性缘叙事被更频繁地表达,这种转变本身及其对现实女性群体自我认知的影响皆具有矛盾性,具体到影片中主要体现在符号的气质表征、“死亡”结局与动机矛盾和两个方面。
1、符号的气质表征:花衬衣、绣花鞋、花束和被丢弃的花
符号代表意义,符号延展意义。50年代和80年代的反特片中皆有不同程度的符号化体现,隐喻了女性气质、回忆和意识形态的矛盾立场。
回看《英雄虎胆》中的阿兰,是全片穿着最具女性气质的角色,她的花纹衬衣无疑是对性别魅力的强调和特务引诱性的隐喻(图14);《雾都茫茫》中贯穿全片的绣花鞋(图15),多次给出特写镜头,在充当悬念的同时,也是背后谋划者女性的身份表征,充满了女性气质。

80年代的反特片在表现手法上比50年代更丰富巧妙。除物以外,“人”也可以作为符号。《雾都茫茫》开篇沈兰已故战友朱玉菀的妹妹朱玉雯的出场,犹如一幕“睹人思人”,朱玉雯作为一个高度相似的女性面部符号将沈兰引入了与朱玉菀的回忆,增添了影片的戏剧性。多年前沈兰和朱玉菀互生好感,但彼此都身负重任,只能暂且搁置儿女情长。这种以符号连接的蒙太奇叙事在《英雄虎胆》等早期反特片中是鲜见的。
上述符号隐喻的是最基本而可见的女性气质,另一种更深层的气质隐喻在《雾都茫茫》中可瞥见一二。沈兰应邀去林家赴宴时带了红色的花束送给林晶,这束花进门后被交给了同样潜伏在林家的朱玉菀安置于花瓶,宴会结束分别时,林晶取了其中一朵红色的花别在沈兰的衣领上,对他说了一句“愿春常在”(图16),沈兰上车后将花取下,看了几眼随手扔出了窗外(图17)。镜头和灯光的特写在那束艳红的花和被遗弃在路边的花之间不经意地完成流转,沈兰手捧着送给林晶的象征浪漫性的花束表面上象征他对林晶的示好和引诱,是他救下林晶后打入林家的“敲门砖”,宴会后他对林晶给他别上的花露出自信而略带轻蔑的微笑,并随手丢弃,却是对林晶真情的践踏,也显露了他的真实意图,呼应了那束花被转交朱玉菀手中的情景:有共同目的立场的战友朱玉菀才是他真正交付信任的伙伴,他是背负着刺探敌情任务接近林晶的,儿女情长不过逢场作戏。花束以讨好女性的情感气质为“明”,以隐藏的革命气质为“暗”,而当林晶想以停留在“明”的方式——那朵花和“希望花永远开”的愿景——回应沈兰的示好时,自然也无法获得同等的真心,就像那多被丢弃的花一样。在此,花束和被丢弃的花通过这串连贯的叙事分别完成了背后各自意义的建构,相较50年代对敌我毫无铺垫的渲染,80年代的反特片在符号表达手法上更加成熟精妙,既暗喻了我方英雄的革命气质和立场的正义性,迎合了意识形态的硬性要求,于观者却也不会丢失那份婉转浪漫的复杂情感。

2、“死亡”结局与动机矛盾:性缘叙事
女性角色的叙事裂隙在反特片中其实一直存在,但50年代几乎没有表达的的空间,能登上台面的表达也因审核极度隐晦,直到80年代才随着社会开放步伐展现更丰富的表达。以女特务为典型对象,“死亡”结局和动机为叙事裂隙的呈现手段,女性角色个体鲜活的一面借此得以脱离固有的集体叙事框架展现出来,具备一定的积极性,但其所转向的性缘叙事模式同时也难免落入男权社会为女性量身定做的另一个统治框架,因此“死亡”结局和动机时常产生矛盾。
“死亡”结局是反特片中特务角色始终延续的一个经典叙事模式,这个模式很多时候不由特务单独完成,而是女特务、男英雄和正义第三方共同完成的。为了凸显女特务作为邪恶敌对阶级的政治非法性并成全男英雄私德的完美,女特务不会被男英雄亲手杀死,而是被第三方杀死。而发展至80年代的反特片,这个模式大部分仍旧延续,在“死亡”方式上则产生了细微的差异。《英雄虎胆》中阿兰的“死亡”结局,是得知曾泰真实身份后面色狰狞地向他开枪(图18),随后剧情设置避免了曾泰亲手枪杀阿兰,而是让赶来的解放军击毙阿兰,完成了意识形态下“死亡”的终局叙事;《雾都茫茫》中林晶的“死亡”结局,则是从船舱里看到外面沈兰带人来抓捕她,悲愤交加服毒自尽(图19),以另一种手段避免了由沈兰亲手接触她的“死亡”,两种剧情设置殊途同归。

“死亡”结局既是意识形态的产物,难免与“死亡”动机,或者说是人物的整体动机发生前后矛盾,女性角色的叙事裂隙由此诞生。《英雄虎胆》的阿兰作为一个女特务,政治归属并未和外表呈现完全的同构性,她妖艳的外表并未与邪恶的内心完全划等号,她对自己的政治立场淡漠,会对抗拒性骚扰,会为自己感到委屈,注重自我感受,只想去海外过舒服的日子。她最初的结局是替曾泰挡枪而死,这是对其人性的复杂刻画,让这个反派人物因“爱情”而生动,也与其人设吻合,最后却因审核限制改为对曾泰开枪被解放军击毙的突兀结局,又因阿兰过于美貌,处于对观众倒戈的担心,王晓棠被要求必须面露狰狞以展示女特务邪恶的“真面目”和其代表的政权的非法性,可见当时社会语境对反特片意识形态的要求之严。从最终成片的角度看,原本心中有“爱”、对政治淡漠的阿兰突然生硬地变回了绝情而对政治极为强硬的坏女人,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迫使影片前后叙事连贯性被打破,阻碍了对人物形象的立体刻画,但导演的叙事、观众的接收反馈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过程却也成为了50年代反特片叙事裂隙的佐证。
相比之下,80年代的《雾都茫茫》呈现出的结局与动机间的矛盾则更为复杂。林晶的人设不同于阿兰这样的传统女特务,她是出身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是“纯良的女儿”,并非从起初就是彻头彻尾的反派,她的身份伴随动机转变,动机则源自经历:遇见并爱上沈兰,信任沈兰却被沈兰利用欺骗导致父亲被逼上绝路,内心从单纯到被仇恨浸染,走上反派特务之路。她的结局呈现时,难免给观众带去充满矛盾的困惑和唏嘘:林晶是邪恶的女特务吗?林晶的死有其正当性吗?如果没有沈兰的欺骗,没有林南轩的死,林晶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林晶所展现的“恶”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恶”还是出于个体的报复?正如林晶曾对陈浩说过的“我爱沈兰,如果他是共产党,我会亲手杀了他”,某种程度上,林晶的“恶”反而是由沈兰一手造成的,沈兰作为我方英雄的私德不再完美。林晶在背后谋划父亲未完成的C-3计划,未必是为了在政治上制造国共对立,而是纯粹的报复,可以是基于亲情为父报仇,也可以是基于爱情对沈兰的报复。从片尾她服毒而死时脑海中闪现对沈兰回忆的画面看,她的动机或许偏向后者。但也因此,民族大义或敌我斗争的对抗意味被覆盖,只留下情场恩怨,让她的“死亡”结局缺乏正统的说服力。
观众对女特务产生的逆反性欣赏和唏嘘越强,影片本身首要注重的政治意识形态灌输就遭遇越大的失败。同为女特务,如果说阿兰的叙事裂隙聚焦于“必死但怎么死”的问题,最终在意识形态的桎梏下舍弃了“为爱舍生”的性缘叙事,林晶的叙事裂隙则直接挑战了根本性的前提——“因爱生恨是否必死?”,此时性缘叙事已在角色刻画中占据半壁江山,与淡化的政治革命叙事分庭抗礼,成为供观众文化消费的热门元素,极大地增添了反特片的戏剧性和娱乐性,通过对女性角色的重构一定程度实现了女性个体的私欲表达,改善了女性刻板印象。
但与此同时,这种性缘叙事的重构又使女性角色堕入另一重新的刻板印象。以性缘关系为中心是男权社会给女性设下的规训,也是对男性统治欲和观看欲的满足,本质上依旧是性别的结构性压迫。反特片对女性角色尤其是女特务的爱情刻画从50年代政治强压下的轻视到80年代的迷恋,女性形象并未真正脱离枷锁。即便在相对积极的叙事裂隙中,阿兰也是为情所困,林晶对沈兰爱恨交加,她们都依托于男人而非自己来构建情感与成长史,主体性实则有减无增。在过去,女性角色被淡化或抹去性别特征,融入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的洪流,作为分辨敌我的意识形态符号。在永远高于个体的集体中,女性没有“自我”,只有“大我”,而当她们终于被允许脱离革命叙事时,个体浮现于宏大叙事缝隙的唯一路经竟只有以男性为寄托的父系叙事和性缘叙事,而缺少自身的独立、成长和力量展示,这于女性在社会文化中的整体地位和身份认同仍是一种朝向“他者”的倒退。
结语
综上所述,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反特类型影片在叙事和表达上经历着微妙的转变,在固有的宏大框架下展现出由弱到强且各具特点的叙事裂隙。通过对《英雄虎胆》和《雾都茫茫》的比较分析,一方面,80年代反特片相较50年代在外在元素、“美人计”、凝视的运用上更加自由开放,体现出意识形态由政治一元化向消费娱乐化、自由化转移的转变;另一方面,80年代反特片的性缘叙事比50年代更加成熟,通过符号隐喻气质,拓展女性角色的个体表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受制于男权统治体系,即便脱离了意识形态的捆绑,也易落入另一种倒退的规训。
参考文献
[1]俞洁《“十七年”中国反特电影的类型研究(1949-1966)》,浙江大学,2012年,第99-102页。
[2]孙樱齐《悖反、承接、超越——从反特类型片到谍战影视剧的叙事流变》,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
[3]檀秋文,彭婧贻《从意识形态宣传到娱乐性追求的蜕变——20世纪80年代反特片研究》,《当代电影》2009年第12期,第68页。
[4]戴锦华《谍影重重——间谍片的文化初析》,《电影艺术》2010年第1期,第62页。
- 1.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第229-255页。 ↩
